|
罗意威包包 无论是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片头里,还是中小学教科书中,常有这样一位女科学家的身影一闪而过。她总与黑猩猩一同出现,举动亲昵,像是两位熟识已久的挚友。 古道尔与黑猩猩 简 · 古道尔(Jane Goodall),英国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剑桥大学博士。自小热爱自然和动物的她,20余岁时只身前往非洲观察黑猩猩。这位当时并未接受过系统训练、自幼在都市长大的年轻女性,顶着外界的重重质疑,在非洲丛林的艰苦环境中开启了自己一生挚爱的事业。 古道尔博士热爱自然,也目睹了破坏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险、不公、种族屠杀..…关于黑猩猩的研究为她打开了一道观察人类之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行善的力量,也存在着作恶的力量”“只要我们能有爱心,不残酷对待人类和动物,我们就将站到一个人类道德与精神演进的新时代的门槛上,并最终实现我们独有的品质:人道主义。” 古道尔初到贡贝 在煤油灯下写手记 本文摘取自简·古道尔的自传体回忆录《点燃希望》,主要讲述了古道尔对黑猩猩敌对行为和领地行为的观测,并由此引发对人类战争的思考。 01 战争,不只是人类行为 ”许多过着平平淡淡生活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在我们的电视、报纸和杂志上,暴力才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黑猩猩能产生与某些原始的人类战争形式不无相似的敌对行为和领地行为。了解这一点既非常有趣,也令人寒心。 我以前一直认为,战争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对于类似战争行为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它似乎是人类群体一个几乎带普遍性的特征。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一些范围非常广泛的问题,包括由文化和知识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至少从生态上来说,战争解决了胜利者获得生存空间和充足资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还起到了降低人口水平、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此外,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史前的战争是群体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冲突,肯定对群体成员之间越来越复杂的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选择性压力。交际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复杂的口头语言的出现带来极大的优越性。智力、勇气和利他主义就会受到高度评价,因而,与群体中胆子较小、技能较差的成员相比,优秀的武士就会有较多的女人,生出较多的后代。这一过程将不断升级,因为一个群体的智能、合作和勇气越突出,它的敌人所受到的压力也越大。 实际上,有人认为战争也许是进化中的主要压力,而正是这种压力使得人类的大脑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的大脑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大脑不太发达的原始人类在战争中无法取胜,因而就被消灭了。 毫无疑问,早期人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发达的大脑。因为人类的大脑比起黑猩猩的大脑要大得多,所以化石考古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介乎半猿半人之间的骨骼化石,以便从化石方面为人与猿之间提供一个联系环节。实际上,这个所谓“失去的环节”肯定是由一系列业已消失的大脑形态组成的,而且每一个都要比先前一个更复杂。对于科学来说,这些大脑除了在有些头盖骨化石上留下过一些微弱的痕迹之外,的确是永远失落了。 只要一想到战争,我们的脑海里往往会出现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运动的情景:骑在马上的、徒步行进的、驾驶装甲吉普坦克的、开着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军人面对着可怕的冲突。更为糟糕的情景是,按下一个键钮,就可以在转瞬之间消灭一个国家。人类的战争是在国家之间,或者一个国家的各个派别之间进行的——其中尤以革命和内战最为惨烈。 贡贝黑猩猩之间的“四年战争”当然无法与人类的战争相提并论,可是它却清楚地说明,这些猿类已经达到只有人类才能达到的战争的残酷性。但毕竟人类历史上大规模部署兵力和武器的能力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如此成熟的。人类的战争也像人类的所有文化进步一样,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从原始的、类似黑猩猩那样的侵略行为发展到如今有组织的武装冲突。现在仍然有一些土著人部落的战争形态跟贡贝黑猩猩的“四年战争”差不多——参加袭击的群体悄悄潜入一个村庄,然后进行杀戮和抢劫。 人类的战争形式是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人类早期祖先的战争形式出现之前,肯定有过许多其他形式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包括群体共同生活和狩猎技能、建立领地、使用武器以及合作制订计划的能力。此外还必然会产生对陌生人的恐惧和仇恨,其表现形式就是侵略性的攻击。贡贝黑猩猩中显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这种特征。 和黑猩猩戴维在一起 黑猩猩的领地意识无疑是很强的。他们不仅保卫自己的林中领地不受来自相邻群落的“外来者”的侵犯——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不过青少年雌性不在此列)。他们每星期至少要对自己家园的边界进行一次巡查,监视其邻居的动向。他们不仅保卫自己的领地,有时还以弱小的邻居为代价扩大自己的领地。贡贝“四年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卡萨克拉雄猩猩产生的受挫感,因为他们不能进入原先属于自己的领地,因为它已被分裂出去的群体所占领。 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有些雄猩猩,特别是那些年轻雄猩猩,觉得群落内部的冲突很刺激。尽管“巡逻队”的其他成员已经离开边界返回,那些年轻猩猩有时却冒险悄悄地逐渐深入,去观察他们的“敌人”。这种带危险性的好奇心也许是早期人类战争出现的重要原因。杀死成年同种成员的情况在哺乳动物中很少见,因为这类冲突对侵略者可能很危险。用文化的方式鼓励人类的武士历来是非常必要的:表彰他们的作用,谴责胆小者,对战场上表现勇敢、杀敌有功者予以重赏等等。 如果人类的男子天生就觉得侵略(尤其是对邻居的侵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士兵的训练就会容易得多。这似乎确实不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总动员的号角一吹响,我们家里的男性成员全都报名参了军。当时德里克还不够当兵年龄,于是他就去了一个又一个飞行训练中心,最后找到一个不死扣条条框框的地方当了兵。人类对死亡和痛苦有极大的好奇,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绞刑示众是很常见的事。 今天(1997年8月),在写这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在德黑兰西部处决一名强奸犯,结果围观的人群有上万之多。他们看着那个人的脖子被套上绳索,然后被起重机吊起来,吊到他们的上方。由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他的腿越蹬越无力,身体扭动也逐渐停止。在观看赛车的过程中,危险的拐弯处往往聚集的人最多。在障碍赛马中,人们最喜欢看的是那些他们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马。公路上发生恶性交通事故之后,会出现数英里长的塞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放慢车速想看上一看。当然,这是因为这些事情异乎寻常,许多过着平平淡淡生活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在我们的电视、报纸和杂志上,暴力才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02 属于某个群体,也有危害性 “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群体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体之间划一道明确界限,挖一条鸿沟,布一片雷区。” 在人类对付同类成员的战争或暴力行为中,有一个重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文化的进化引起了伪物种形成的发展。简单地说,伪物种形成就是,在某个特定群体的一代成员中,个体所获得的行为被传到下一代。经过一段时间,这就形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文化(习惯和传统)。 人类的伪物种形成(我主张用“文化物种形成”来表述)主要意味着一个群体(本群体)的成员不仅会把自己看成与其他群体(外群体)成员不同,而且对本群体和非本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文化物种形成的极端形式会导致对外群体成员的非人化,以至于把他们几乎看成是异类。这就使得群体成员不受群体内运行的禁令和制裁手段的约束,使他们得以对“那些另类”采取在群体内无法容忍的行动。奴役和折磨是一个极端,而愚弄和放逐则是另一个极端。 从贡贝黑猩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物种形成的前兆。他们的群体意识很强;他们对“属于”本群体的成员和非本群体成员加以明确区分。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受到保护,而非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则被杀死。这种群体意识非常微妙,它不是一般的生客恐怖心理。 在发生分裂之前,卡哈马群体的成员和他们的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友善;有的甚至是一起长大,一起漫游、觅食、玩耍,相互梳理毛发,并在一起睡觉的伙伴。卡哈马群体的分裂行为,似乎使他们自己丧失了被看成群体成员的“权利”——他们被当成了“陌生人”。对这些以前的朋友所发动的攻击可以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我们人类的内战一样。 那些攻击大多数都是非常残酷的,但在我看来,最残酷的是对我的老朋友“歌利亚”的攻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歌利亚”会和南边的一伙走到一起。他当时已经老态龙钟,十分瘦弱,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他千方百计想躲藏起来。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躲在浓密的灌木丛中。他被拖出来的时候哇哇大叫。参加攻击的5只成年雄猩猩,以前都跟他关系很好。一只未成年猩猩乘机冲上来用小拳头打他,嘴里高兴得吱吱哇哇乱叫。他们的攻击持续了18分钟,猛打猛咬,乱拖乱拽,把一条腿一拧再拧。他们近乎癫狂地离开之后,“老歌利亚”想挣扎着坐起来,但又倒在地上,浑身颤抖着。虽然我们找了他一个星期,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卡萨克拉雄猩猩一再对卡哈马猩猩发动攻击,所使用的攻击模式在群落内部打斗中从未见过,但却常见于黑猩猩对付大型猎物,使之失去抵抗能力、并将其肢解的过程中。卡哈马群体那些倒霉的成员不仅遭到拳打脚踢,被踩在脚下,而且被打断筋骨,撕开皮肉,四肢被拧了又拧,就像我们看到的“歌利亚”的遭遇一样。在受到集团攻击时,他们被往死里打。其中有个攻击者甚至喝了他的受害者身上的血。卡哈马黑猩猩的确被当成了猎物来对待——他们被彻底“非黑猩猩化”了。 不幸的是,“文化物种形成”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中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平。我们往往形成一个经过挑选的“本群体”,把那些与我们种族背景、社会经济形态不同,政治上不一致、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排除在外。这便是战争、暴乱、团伙暴力以及其他各种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发现人类组织本群体倾向的许多例子,把我们的城市、小镇、村庄、学校或者邻里中的一些人排除在外。孩子们会很快组成这样的排他性群体,抱成一团,相互支持,使自己和其他人之间产生距离。组成这种群体的孩子可能会对“外面的人”非常残酷,有些孩子因此而吃了很大的苦头。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小说,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定的(或者说在错误的)条件下,孩子们的行为可能会变得非常野蛮。 《蝇王》,戈尔丁著,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一些现代团伙可怕的演变过程中,“文化物种形成”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像洛杉矶的克里普斯帮和血盟帮,已遍及世界,他们具有相同的肤色、文身图案和其他有别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区别。他们只不过是人类“文化物种形成”所产生的丑恶事例之一。 古道尔在贡贝森林中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研究了黑猩猩的侵略行为和人类暴力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组织“本群体”和“外群体”时的许多弊端。 在卢旺达、布隆迪、以色列、巴勒斯坦、柬埔寨、北爱尔兰、安哥拉和索马里,都存在着种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仇恨。因种族灭绝或者叫做种族清洗而丧生的人成千上万——不,有上百万。 在德国,由于一个人的上台,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恐怖的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其策划之周密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的确,当希特勒疯狂的杀人计划在公众中传开之后,整个自由世界都认为,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决不能再重演。 不同的宗教群体从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他人,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感到特别震惊。历史上由于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数不胜数。那些所谓的圣战的结果,总是当时的胜利者给那些异教徒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痛苦。我上学的时候,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罗马天主教西班牙宗教法庭的酷刑故事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不过,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教导的核心确实是要求人们放弃暴力,去团结而不是排斥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虽然我没有正规地研究过宗教,我读过《圣经》,听过布道,特别是听特雷弗的布道。我所感悟到的是,耶稣对“本群体”的危害性非常敏感。他毕生都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同情圈,把它扩大到包括所有种族、教派、社会阶层的人,甚至包括为当时的人所痛恨的罗马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还忠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关于忍让和容人的类似教导在东方的经典中当然也不乏其例。 古道尔童年时期全家福 我认为“文化物种形成”显然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成长起了破坏作用。它妨碍了思想的自由,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禁锢在我们所诞生的文化之中。只要我们把自己禁锢在这种文化的思想牢笼之中,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如人类家庭、地球村、团结各民族等等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们至少意识到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知道这一点,还是令人欣慰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身体力行”,那么种族主义、偏执、狂热以及仇恨、傲慢、欺侮显然还会大行其道。(而且也的确如此) “文化物种形成”显然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只要我们继续把我们自身狭隘的群体成员资格看得比“地球村”重要,我们就只能使偏见与无知进一步蔓延。属于某个小的群体自然是没有害处的——对具有狩猎——采集群体意识的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宽慰,它使我们有了值得信赖和绝对可信的圈内朋友。它还能使我们达到心理上的平静。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群体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体之间划一道明确界限,挖一条鸿沟,布一片雷区。 03 只有我们人类,才那么邪恶 “黑猩猩最恶劣的侵略行为跟人类的邪恶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本性中的阴暗和邪恶面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在有些情况下的侵略行为是受了天性的强力驱使。这些情况与驱动贡贝黑猩猩的侵略行为是一样的——忌妒、恐惧、复仇、争夺食物、配偶或领地等等。 此外我还知道,猿类在生气的时候,体态和手势都跟我们的十分相似——摆出傲慢姿态,把脸沉下来,动手打,动拳头,用脚踢,又抓又挠,拽头发,跟在后面追赶等。他们还扔石块和棍子。毫无疑问,如果黑猩猩有刀枪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也会像人类一样去使用的。 可是,人类的侵略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很独特的。虽然黑猩猩似乎对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有所知晓,他们肯定没有人类做得那样残忍。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故意给活着的生灵造成身体上或者和心理上的伤害,尽管我们知道——甚至正是由于我们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 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我们人类才那么邪恶。正是我们的邪恶,使得我们在过去的千百年中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坏招,使千百万活生生的人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因此,我清楚地看到,黑猩猩最恶劣的侵略行为跟人类的邪恶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类必须永远做自身邪恶基因的奴隶?当然不是。跟任何其他动物相比,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肯定能控制我们的生物本性?难道关爱和利他不也是我们人类从灵长目那里继承来的吗?我在想,不管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爱的根源来自何处。 本文节选自 《点燃希望》 作者: [英]简 ·古道尔 / 菲利普·伯曼 译者:祁阿红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21-5 页数: 265 编辑 | 梦奇 主编 | 魏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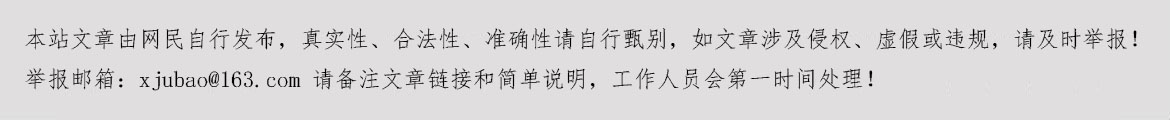
|
|
1
 鲜花 |
1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业界动态|丹东生活网

2024-04-16

2024-04-16

2024-04-16

2024-04-16

2024-04-16

请发表评论